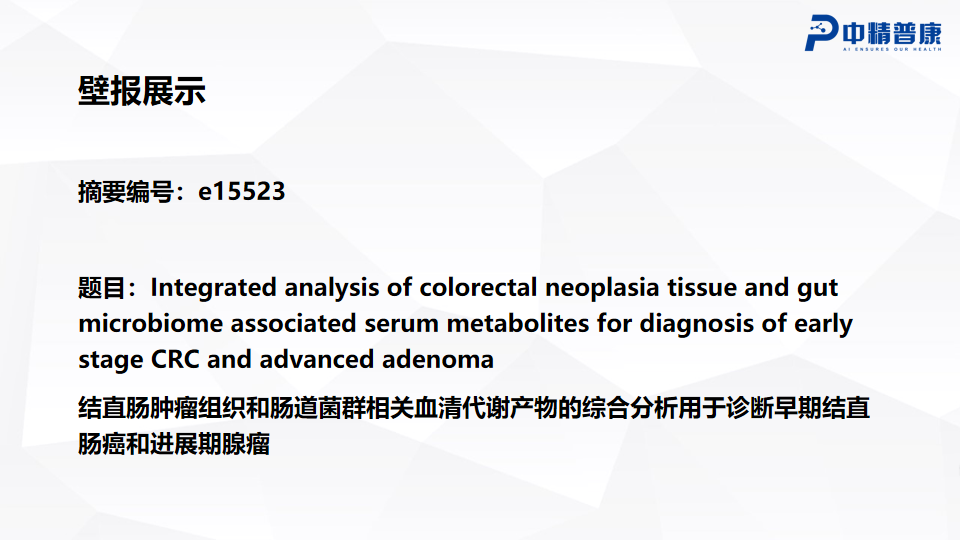王学圻:我常常会想,某句话我是不是应该再说得阴阳怪气一点
在空政话剧团跑了多年龙套,电影《黄土地》一战封神,此后的《天地英雄》《梅兰芳》《十月围城》……几乎从未失手。有人说,王学圻是越活越帅,其实一直支撑他的是性情中军人特有的简单和有目标。2019年,一部话剧《爸爸的床》,让王学圻时隔20多年重归舞台,如果不是因为疫情,这出戏原本10月底在国家大剧院将有四场演出,但遗憾的是,仅仅演了两场便收场了,可这两场却勾起了他对当年军旅话剧生涯的回忆……
观众说:看完戏回到家,正好爸爸来电话,第三句话说的就是剧中的台词
“最近忙吗?”“天气怎么样?”一对父女在电话中的对话就这样开场了,尴尬但似乎又很亲切。2019年,由沪上制作体椎·剧场出品的话剧《爸爸的床》因有王学圻出演而备受期待,那一次北京的演出是在超剧场。多年未回话剧舞台,王学圻没有敲锣打鼓,而是默默地演起了小剧场。“这个戏写得太特殊,我从来没演过这样的戏,该怎么演其实最早也不知道。导演也没导过这样的戏,剧组的每一个人都是开动脑子慢慢琢磨着、磨合着。”
舞台上,一个妻子去世后再娶的父亲,一个失去母亲对父亲新生活极为抵触的女儿。父女俩自始至终在打电话,女儿从未踏进过父亲这边自己曾经的家,而父亲也未去过女儿的那方天地。满台的箱子既是父亲正在将旧物打包,又可垒砌成父女关系中一道隔阂的高墙。王学圻说:“由于父女两个人不是在同一时空内正常的交流,我们越演越觉得编剧编得好,翻译翻得好。看起来只是对话,但弦外之音却能让观众感受得到,但也正是因为不见面,话里有话就需要通过表演展现出来。实际生活里也是这样,只是我们不去在意,我和我儿子也有过类似的对话。电话中每一个‘嗷’都表达着不同的意思和想法,你来我往间,慢慢就有了那种细腻的感觉,味道也就出来了。其实剧中父女两人间的关系没那么简单,但也没那么糟糕。有时两人突然沉默,是因为都想起了当年的一些小事。”
从首演至今,王学圻觉得很多开始被忽略的东西如今都慢慢找到了。而这二十几通电话如何能把每一通都打得不一样,也着实费了一番心思。父女俩的台词很多,每一句怎么说,都经过了反复的斟酌,就是希望传递给观众平静对话背后两人的思考。“我很佩服这个戏的编剧,把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写得如此有想象力,甚至让人揪心。亲情之间的表达,只有身在其中才知道该怎么说,不在这根纽带之上,很多话可能说不出来,而且很多话也只有女儿能这么说,儿子都不是这样的表达方式,编剧真是太细腻了。我们在上海演出,第二天就有个小伙子在网上发文,说看完《爸爸的床》回到家,正好爸爸来电话,第三句话说的就是剧中的台词,当时他就哭了。我们生活中这样的情况太普遍了,父母和子女在两地,聊不了两句就没话了,只能问问天气,看起来云淡风轻,实则暗流涌动。”
剧本中没有“你个兔崽子你也不回来,不要你老爹了”这种特别强烈的对话,而是父女间那种淡淡的表达
荷兰的编剧,德国的导演,法国的舞美设计,《爸爸的床》中如此国际化的创作团队不仅没有带给王学圻观念上的冲撞,反而让他对父女关系这一世界性的话题多了来自国际视角的认知。“第一次跟导演见面,我以为他是导演的助理,边聊边等,我心里嘀咕怎么导演一直不来,也不好意思问。就为了‘等’导演,聊了4个小时,人家也插不上话,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。后来工作起来才发现导演也是对生活非常敏感的人,他会按照你的习惯去启发你,根据你熟悉的方式再延伸。整个过程非常和谐,导演也从来不发脾气。”
王学圻称赞德国导演的英语不错,简单的几个单词,就能明白他的想法。“ 比如我演一遍,他只要说‘Mr Wang’(王先生),我就明白了,我刚才演得肯定不到位,应该再强烈一点或者是再减弱一点,他一比划我就能懂。我能感觉到,他看我们的表演是很享受的。在他看来,父女之间的交流屏障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,在他们国家依然存在。孩子大了外出工作,父母年龄大了则需要照顾和心灵的抚慰,但孩子顶多就是来个问候的电话。国外更是如此,剧本中甚至没有‘你个兔崽子你也不回来,不要你老爹了’这种特别强烈的表达。剧中的父亲没有埋怨女儿为什么不回来,他们的分歧就在于女儿对这个继母的抵触,这种情绪只属于父女,男孩子都不会是这样的表达方式。”
在王学圻看来,“这种两代人之间的交流屏障问题今天非常普遍,我们不能解决,但却可以通过作品给人力量和勇气,再忙再累,也不要忘记亲情。有一次,我的司机就跟我说,每次给父母打电话其实也没事,就是觉得不打不合适,听妈妈说她种了点茄子,之后每次打电话都会问您的茄子怎么样了?”
我常常会想,某句话我是不是应该再说得阴阳怪气一点,这样才能让观众看到角色内心的活动
来自法国的舞台设计用箱子装点的舞台,在王学圻的眼中充满了丰富的想像力。“这个寓意就是把过去装进箱子,还有剧中提及的帽子和茶具,其实都象征着过去,父亲想把过去全部装进箱子,以这种方式预示着要去迎接新的生活。因为这些旧物就会让他想起自己的妻子,过去的生活也就一直过不去,他对过去其实是太爱惜了,但女儿不理解,觉得他对妈妈的爱没有了,这个矛盾一直纠缠着两个人。”
全剧的结尾,两个人推倒箱子最终见面。“其实爸爸是太爱妈妈了,念念不忘,以至于没法生活下去,但女儿不依不饶,最后听到了父亲在电话那边的哽咽心酸,才理解了那种怀念……女孩子一般跟妈妈会话多一点,但她的妈妈又过世了,就这么一个父亲,她极力想寻找家庭的温暖,这就构成了父女关系这个经典的话题。父女关系最经典的剧目是《李尔王》,这个看似简单的家庭关系,其实却是一个能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的话题,每一个碎片其实都是我们生活的日常。开始看剧本时我想得特别简单,但是到现在,每次看剧本我都觉得越来越复杂,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都值得琢磨,我常常会想,某一句话我是不是应该再说得阴阳怪气一点,这样才能让观众看到角色内心的活动。这样一台两个人不打照面全是打电话的戏,看似观众在台下看得很安静,实则是需要一起思考的。”
这些年话剧演得不多,因为时间关系,王学圻看得也不多。“但这个剧本我看了之后觉得很有想法,当时就是觉得很现实又很简单,而且剧本翻译得非常好,他们椎·剧场的团队大多拥有海外留学背景,对最前沿的戏剧了解很多。而且还会有戏剧构作对剧本进行梳理,所以读起来你既能感觉到地道的京味儿,又透着国际视角。”
遮遮掩掩费半天劲想出来的细节,如果年轻人说不是我们这代人的思维,我会果断剪掉
当年的空政话剧团不仅有“军中明星团”的名号,戏剧观念之先锋,在全国戏剧院团中都是旗帜一般的存在,其中《WM我们》,至今仍是戏剧院校导演系教学绕不过去的早期先锋戏剧代表作。
最早《爸爸的床》的制作人找到王学圻时,还曾经担心他不能接受这种戏剧形式,而王学圻就给他们讲了当年在空政演的那出《WM我们》。“那个戏里,我们可以瞬间变成几棵树,表现地震后的废墟使用了一个巨大的镜框,这种处理方式,当时在全国都很轰动。1987年我第一次出国去蒙特利尔电影节,大冬天的,组委会组织的晚会门外站着两个金发碧眼穿着很单薄的姑娘,做着机器娃娃一样的动作,你冲她招手,她也跟着学。后来排《凯旋在子夜》的时候,有一个场景是我们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被冻僵之后,我就借鉴了在蒙特利尔看到的这两个姑娘的动作。那时的空政话剧团,戏剧观念很先锋,《WM我们》的导演王贵真是太有才华了,音乐、舞蹈他都懂,我们排《陈毅出山》,里面有一段拉纤的号子竟然也是他写的。所以对于国外主创团队的创作方式,我一点都不陌生。”
而对于和年轻人的合作,王学圻也从不以经验和资历压人。“有一次在外面拍戏,我绞尽脑汁想了很多细节,但后来年轻的主创们说,王老师,这不是我们这代人的思维。我果断地说,全剪掉。我特别能接受,现在的作品一定是给当代人看的,这段情节我遮遮掩掩费了半天劲,又用煽情的音乐烘托,最后观众不理解,说:您这干吗呢?这种结果我坚决不要。”
那时空政著名的“龙套三人组”一晚上的服装比主演都多,说明书上的名字永远是“本团演员”
如今,当年空政著名的“龙套三人组”个个都是数得着的人物,除了王学圻,李雪健是中国影协名誉主席,濮存昕更是现任的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剧协主席。当年,三人关系最铁,王学圻回忆,“他们俩都有专长,雪健打扫卫生一门灵,小濮出黑板报,每到周六就光着膀子出板报,政委、团长一吃饭都看得见,说这青年不错,写得一身粉笔末,很悲壮。”
后来李雪健、濮存昕相继离开空政去了国家话剧院和北京人艺,王学圻始终坚守。“其实我们三个里,说起军旅题材的作品,我比他们俩更适合,我的气质更像是部队的,演个飞行大队长、飞行团长没什么问题。小濮太文了,雪健有点像坏人,即便演文书也是个坏文书。我演红军甲,他一定是匪兵乙,基本就是他把我打伤,我再把他打死。很长一段时间,我们三个在说明书上是没有名字的,我们就叫‘本团演员’。那会儿只要一演戏,我们仨最忙活,光跑群众的衣服就一大堆,雪健说,哪个主角有咱们衣服多,人家也就一两套,我们这一晚上改好几次装,一会儿改个北伐军,一会儿又改个背矿石的老百姓,来回跑。现在想想其实挺好玩的,那时我们特别团结。大家都在团里生活,跟现在社会上的状态完全不一样,认真的空气之浓从一进院就能感受到。早上不到8点就到团里,一小时台词、一小时形体,我们团也有泳池,还能运动。后来还弄了个健身房,买了好多器械,给大家发衣服发鞋,头3天人倍儿齐,第4天开始就没人去了,头疼屁股疼、腰疼胳膊疼,到最后就剩我们三四个人了。那个年代我们是需要天天练功的,专门发的有练功服、灯笼裤、练功鞋,还有练功的板带,姑娘们一个个也在院里每天一小时练得可厉害了。后来中戏姜文那个班的台词老师都是我们空政过去的。”再后来,王学圻在《陈毅出山》里演了一个烈士的角色,李雪健感慨,“行了,咱几个人终于能演有名字的了。”
那时我们一年四季都是军装,第一次买牛仔裤总觉得紧
在灯市口同福夹道空政大院住了多年,每天听着隔壁学校的铃声,但现在再进那个院子,已经物是人非了,王学圻脑子里的那个大院还是原来干干净净,有太湖石、有游泳池,一群穿着军装的少男少女们迎面走来的样子。“那时候一集合,小姑娘、小小子,一个个精精神神,而且业务学习特别充实,杂念少、诱惑少,思维也简单,不管是下部队还是在团里,大伙在一起就是琢磨戏。那时我们哪考虑过钱,连衣服都是冬天了就领冬装、夏天了就领夏装,黑板上只要不写明天换冬装,冻得打冷颤也得穿着夏装。吃饭、集合都是听安排的,只有排戏时需要动脑子。”
20多年前,演完一出《横空出世》之后,王学圻20年没再上舞台,却选择了一出小剧场悄悄地回来了,对于为什么没有选择大经典大制作,王学圻说,不是没有找过他,确实是因为时间不合适,例如《简爱》就曾经邀请过他。“我是舞台上成长起来的,我喜欢话剧,像我、雪健、小濮,我们几个人都是在话剧上滚出来,确实是有感情。”很多人都淡忘了王学圻还曾经是戏剧“梅花奖”得主,那还是一部名为《特殊军营》的军旅戏剧。如今偶尔遇到当年的战友,他会特别感慨,感叹大家都画了老年妆,但唯一不变的是他们还是会沿用当年在剧中的称呼,比如“秀子”。
因为《爸爸的床》,王学圻第一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,或许是因为对舞台的那份眷恋,当年空政话剧团的仅有10米宽10米深的剧场在他的记忆中都好得不得了。“虽然剧场里没有那么多吊杆,我们还是为能有个自己的舞台高兴得不得了,《周郎拜帅》就是在那排的,后来大家都知道的《炊事班的故事》也是在那拍的。”
那时的空政话剧团,满地金子的成色甚至不亚于北京人艺,王学圻因为担任领导,总要面对演员申请出去拍戏的事,“我总觉得人家在团里跑一群众,在外面可能演一主角,是难得的锻炼和实践,在外面演出了名气,再回来演话剧,对团里也好。”

那时,他还要管很多生活琐事,新调来的演员要谈心,还有某个女演员做了双眼皮手术,甚至某个男演员穿了件什么衣服,都要关心,“那时洪剑涛是最时尚的,大红短裤配一件大背心,上面是一个男孩和女孩接吻的照片。那个年代,我们一年四季都是军装,记得那年脱军装时,我们有很多老同志穿着牛仔裤都不敢进礼堂。我自己也一样,第一次买牛仔裤时总觉得紧,因为我们军装都是宽腰的。”
到现在,王学圻还留着当年的军装,“那时我最喜欢海军的衣服,特别是水兵的帽子。”